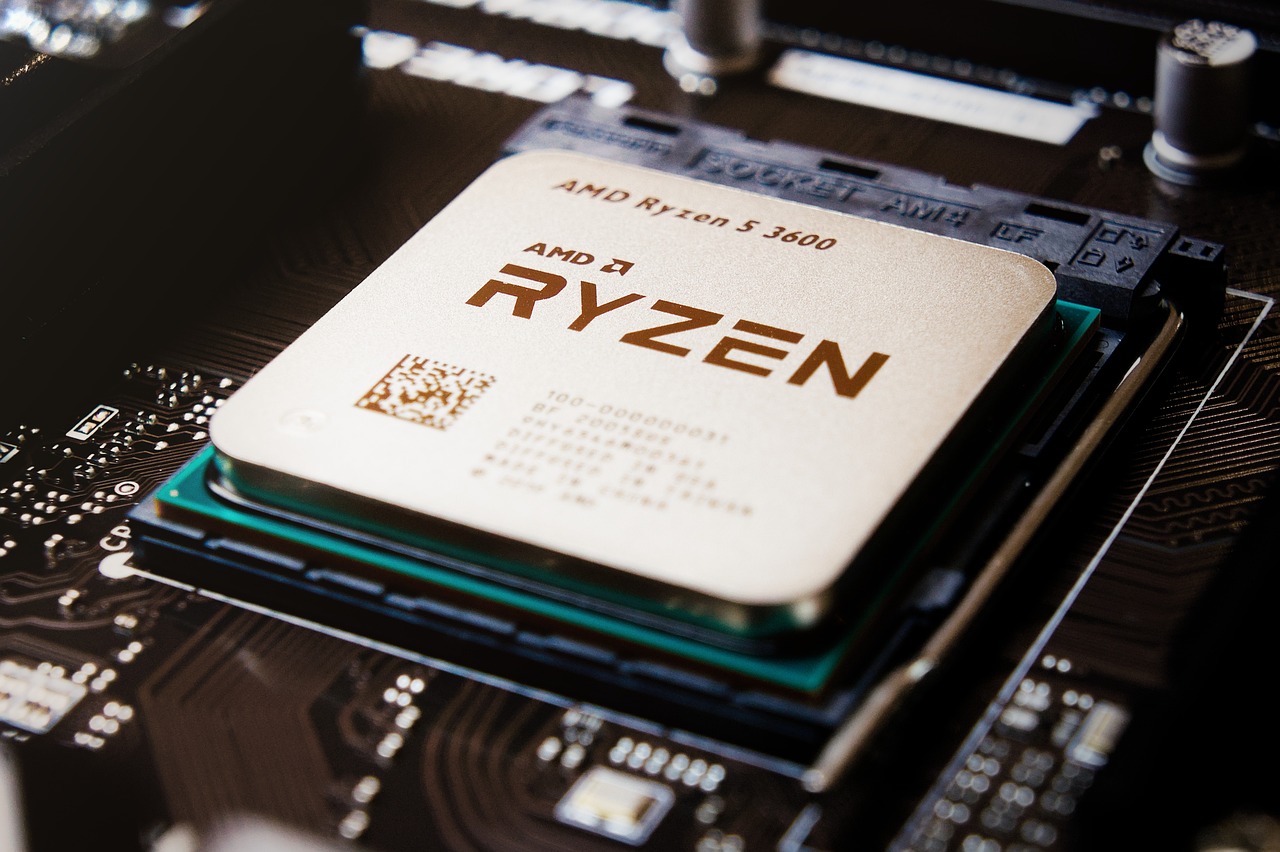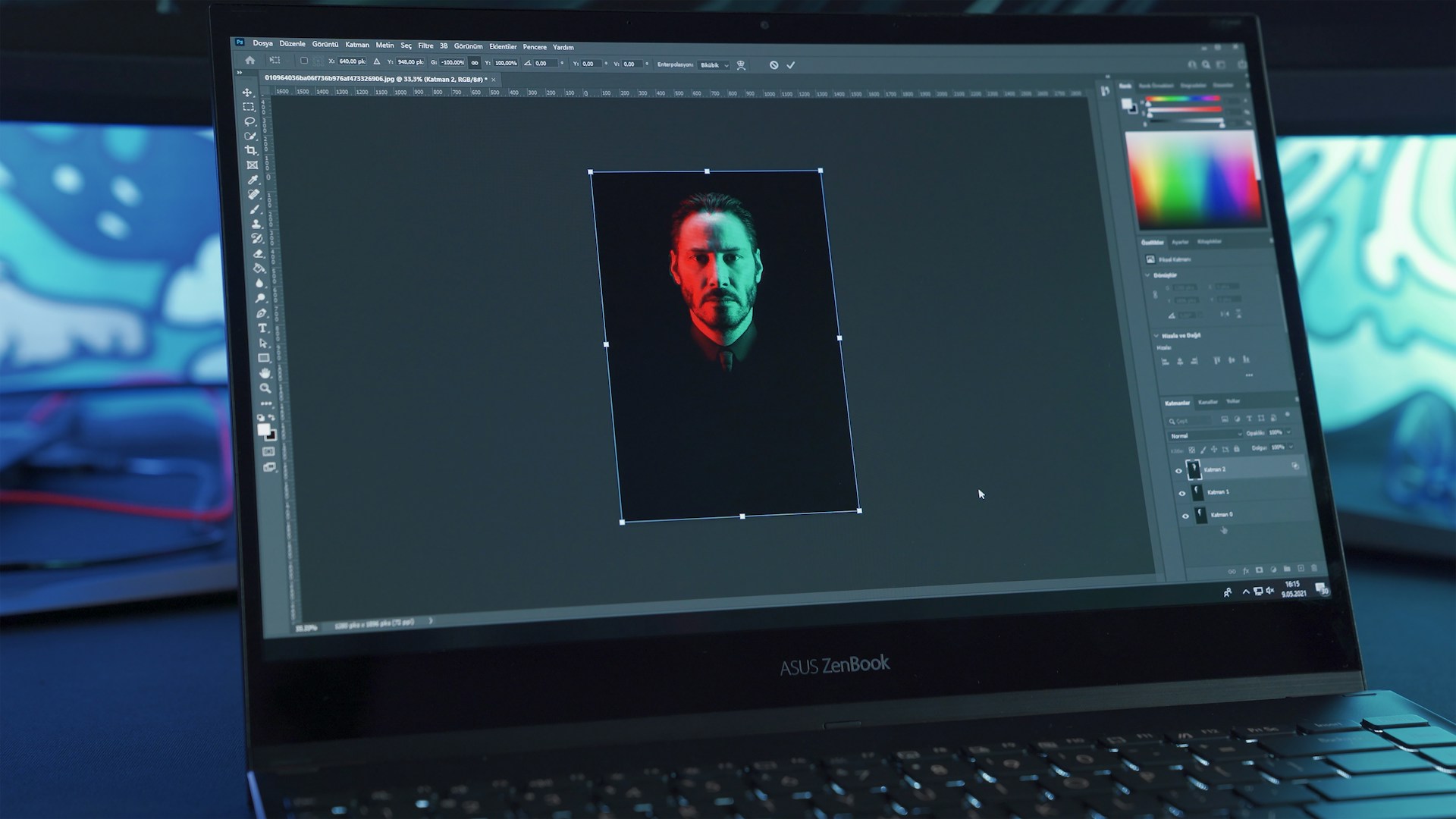大多數感受都比表面更深。它們植根於最初使該事件成為故事的環境下的某些東西。大多數感覺都不是真的。在某種程度上,它們誕生於一段歷史,對許多人——不是大多數——來說,什麼比真相更重要。
以巴黎圣母院為例。請把他們從大學橄欖球季后賽中淘汰。以馬庫斯·弗里曼(Marcus Freeman)“恰巧”擔任教練為例。
一年前,NCAA 橄欖球界慶祝了黑人教練的進步,兩名黑人教練首次帶領他們的項目參加 CFP 的比賽。這個賽季,情況發生了變化。並面對這個改變的機會:當然,是一位即將成為的教練。 。 。黑色的
相信:聖母大學體育總監皮特·貝瓦誇(Pete Bevacqua)並不是這個ND故事的最前沿——弗里曼才是。更重要的是,弗里曼的臉。
去年,愛爾蘭戰鬥隊參加全國錦標賽為學校帶來了 2000 萬美元的收入,主要是因為他們參加的會議不需要與任何人分享行李。錢,全部。
NCAA 的所有體育總監都厭倦了 ND。其他學校甚至可能有一半的國家討厭 ND。大學橄欖球季后賽委員會似乎也不是最大的粉絲。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愛爾蘭人今年未能進入 CFP 與弗里曼以及他在全國最負盛名、最有價值和最強大的足球學校中擔任的職位無關。
但這都是巴黎圣母院還是馬庫斯·弗里曼的作品?這是肯定的 感覺 比另一個多。 ND 並不認為自己因為弗里曼是黑人而“受到羞辱”,但是 感覺 他的膚色和大學所受到的待遇之間可能存在某種聯繫——無論是戰略上的還是偶然的——這是一種內心深處的感覺,即使我們看到證據來反駁這種感覺,媒體上似乎沒有人大聲喊出來。這是不容忽視的。
“這並不是因為他們是黑人,”世界在這些案例中告訴我們。他們只是“必須是黑人”。我們的回應是: 然而,為什麼這些事情總是發生在我們身上,因為當這些事情發生時我們只能是黑人呢?
(同樣的情緒可能適用於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的詹姆斯·富蘭克林,但不適用於密歇根州的莎朗·摩爾。我們離題了。)
“這是我第一次認為聖母大學因為沒有參加會議而真正受到懲罰,”體育分析師喬什·佩特在“喬什·佩特的大學橄欖球秀”上說道。
嗯。 。 “第一次”作品。 ND 獨立於會議已近 100 年。有趣的是,當一個人處於“黑人”中心時,這些“第一次”往往會發生。不知怎的,這種感覺更加鞏固了,“該死,我們又來了。”
因為對於那些感覺自己與故事的效果有直接認同和聯繫的人來說,人性的反應是不同的——尤其是那些外界的聲音不斷告訴你,你的感覺是假的。當熊隊告訴我們“布萊克”與洛維·史密斯被要求離開哈拉斯大廳無關時,我們不應該有某種感覺。當聖母大學告訴我們“黑色”與泰·威林厄姆前往南本德無關時也是如此。當威利·塔格特在佛羅里達州立大學不到兩個賽季的“黑人”成績為零時也是如此。
同樣受人尊敬的聲音同樣帶著高尚的國家的優雅,告訴我們“黑人”與對科林·卡佩尼克表現出任何“正式興趣”無關,也從未被 NFL 球隊正式徵召參加比賽,但菲利普·里弗斯在年僅 44 歲的時候就被召回重返 NFL,儘管他已經離開了五年。
(當我們談論白宮決定在馬丁路德金生日和六月節結束全國國家公園的免費日時,我們從同一個人那裡聽到了同樣的話。
種族與膚色無關,而與聯繫有關——人們對某些人以及與這些人有聯繫的人的感覺,因為他們的膚色,而且往往是因為他們的種族傳統和共同的歷史。當我們的色彩上升到我們情感的頂峰時,同情心、同理心、尊重和情感理解都與情感聯繫在一起。
即使感情並不真實。尤其是當信息既是主觀的又是選擇性的時。有許多合乎邏輯和不合邏輯的理論流傳開來——CFP委員會正在重組下賽季的賽制,以避免針對弗里曼離開ND並將他的才華帶到NFL的反壟斷訴訟。
一切可能都是不真實的、不露面的。沒有種姓,但因情境而不停歇的感情。
“巧合”這個詞可以有多少種不同的用法? “水”字怎麼樣?沉默的真理生活。至少看起來是這樣。這些感覺可以被視為錯誤的,但絕不是毫無意義的。